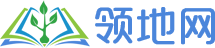田野里,一抹残阳
田野里,一抹残阳
落日的余晖,抖抖地铺满了古老的河畔。

我顶着徐徐吹来的微寒的晚风,漫步于暮色沉沉的田埂上......
我看见,田野里镶着一尊古老的“雕像”。
他弯着腰,用耙细细地、密密地耙着麦田。一会儿,他直了直也许发麻的腰,拭去了脸上的汗水,凝神地望着那转瞬即逝的残阳。此时,我不觉满怀激情端详他的面颊----那是满载岁月艰辛的图谱,那是艰辛对他无情的馈赠,也是艰辛最得意的雕作,更是那汗水印下的伤痕,那是深沉的爱的永恒----刀刻的永恒。总之,这是一幅刀刻板雕的菱角分明周文纵横的脸,是一幅浓缩的地质文图......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呼出了一串串沉重的迷茫,又弯下了腰。我此时觉得,他是那样的痛苦,这转瞬即逝的残阳,毕竟给了他一点点隐隐的不快。就这样,他执着地耙呀、耙呀,我的思绪伴随着他那有节奏的喘息声,飘曳到很遥远的地方,卷入悠远回荡的浪涛......
残阳,最能说明过去的无私和风烛残年的傍晚对大地的一腔痴情。他也就要去了,但仍将一抹微弱的余晖忘情地洒进脚下孕育幸福的每一寸土地中。人世间,唯有他和土地的关系就像残阳与地球的关系一样缠缠绵绵、情愫无尽。他只知一味地将幸福雕琢,而从不计较自己的归宿是凄凉还是壮丽。这真是“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啊!
哦,弱残得崇高,弱残得伟大!
太阳已经下山了,一切都安逸舒适地睡去了。茫茫的幕褐泛起了思索的浪涛,一切都模糊了。他拖着疲乏的身子、迈着沉重的步伐,无憾而归了。我望着那巍巍的背影,似乎明白了什么。
哦,田野里,仍拥着一抹火热的残阳......
。
我顶着徐徐吹来的微寒的晚风,漫步于暮色沉沉的田埂上......
我看见,田野里镶着一尊古老的“雕像”。
他弯着腰,用耙细细地、密密地耙着麦田。一会儿,他直了直也许发麻的腰,拭去了脸上的汗水,凝神地望着那转瞬即逝的残阳。此时,我不觉满怀激情端详他的面颊----那是满载岁月艰辛的图谱,那是艰辛对他无情的馈赠,也是艰辛最得意的雕作,更是那汗水印下的伤痕,那是深沉的爱的永恒----刀刻的永恒。总之,这是一幅刀刻板雕的菱角分明周文纵横的脸,是一幅浓缩的地质文图......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呼出了一串串沉重的迷茫,又弯下了腰。我此时觉得,他是那样的痛苦,这转瞬即逝的残阳,毕竟给了他一点点隐隐的不快。就这样,他执着地耙呀、耙呀,我的思绪伴随着他那有节奏的喘息声,飘曳到很遥远的地方,卷入悠远回荡的浪涛......
残阳,最能说明过去的无私和风烛残年的傍晚对大地的一腔痴情。他也就要去了,但仍将一抹微弱的余晖忘情地洒进脚下孕育幸福的每一寸土地中。人世间,唯有他和土地的关系就像残阳与地球的关系一样缠缠绵绵、情愫无尽。他只知一味地将幸福雕琢,而从不计较自己的归宿是凄凉还是壮丽。这真是“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啊!
哦,弱残得崇高,弱残得伟大!
太阳已经下山了,一切都安逸舒适地睡去了。茫茫的幕褐泛起了思索的浪涛,一切都模糊了。他拖着疲乏的身子、迈着沉重的步伐,无憾而归了。我望着那巍巍的背影,似乎明白了什么。
哦,田野里,仍拥着一抹火热的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