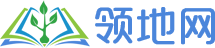评书永不死只是待创新
评书永不死只是待创新
五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师傅是在隔壁村的村口。
雨过天晴,隔壁村路口有些泥泞,贪玩的我也不知怎地就跑到这里。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悉数放在板桌上。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有时候他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吶喊。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键处把惊堂木一拍,围观的村民拍手叫好,有几个放下些纸币在笸箩里。
我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没错,我被评书迷住了。再后来,那个村口的说书人成了我的师傅,他姓孙。
接着便是每日要练功,枯燥无味的口齿训练:喷、弹、啃、吐、磨。唇、齿、腮、喉、舌,五位相结合。转眼,便是几年。
评书就是一个人要演一部电影,要做到一人分饰多角。比如说两个人要打斗了,我必须要扮演这两个人:就见金甲朝着史大奈面门就是一拳,史大奈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来了个小缠捣住金甲的手腕子,借势就顺手牵羊往前一带,跟着脚下是个扫堂腿。
评书这样的民族瑰宝正在一点点过去,去年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突然离世,震惊了整个曲艺界。被大家所熟知的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八十一岁,田连元七十四岁,刘兰芳七十一岁,而所谓的后起之秀呢?屈指可数。窗外风轻树静,我回忆着数年伏案苦练的评书,仿佛听到了晨钟暮鼓里的“来者为谁?花木丽!身居何职?马童是也!”
评书之路,何去何从?
只有评书吗?很多边缘的传统艺术也是一样,只有在大家离去之时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但是很快又忘却了,而这些纤弱的传统艺术如不加以浇灌,将被时代的车轮重重碾压,碾成打印机的铅粉,在教科书上、在宣传册上,追忆曾经的辉煌。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淡如白花素茶的文化空白中振兴发展,没有一种文明能在平淡如流的思想中触及灵魂。没有百家争鸣的激烈、十家九流的异彩,哪里有春秋战国的文化胜世;没有文学革命的激进、文学巨匠的热情,哪里有现代文学丰硕的果实;没有甘洒热血、为国捐躯的热烈的精神,又哪里有我们今日幸福美好的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很多事情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传统艺术是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希望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为评书找到一个新的形式,新的出口,让评书焕发出应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