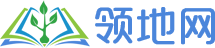火焰背后的村子
发布者:邻家小师弟
时间:2022-11-15 22:35
在真正的乡村,他们留下自己的火焰。不是电灯,不是一次性打火机,甚至不是火柴,是炭薪上珍藏的火,火成为种子,继而成为火焰。
在灶塘里,在堂屋的火炉坑里,埋下火种,时间变成灰烬,灰烬下面是火的种子。每顿乡下的汤汤饭饭完毕,灶膛里最后不用退出的火炭,留成了火种。堂屋火炉坑里的火种亦然,在乡下的夜色深静,狗声停吠,最耐守夜的老人都打起接二连三的呵欠之后,没烧尽的劈柴退出,红火灰里的火种留下。火种被燃烧过的炭灰掩埋,进入时间的深处,缓慢地燃烧或发酵。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乡村?他们习惯留火种,习惯再次需要火焰的时候,用干燥的柴草引火。刨开灰烬,让火种与柴草接触,用昨天的火种引燃今天的火焰。然后火焰穿过劈柴,与劈柴一起酝酿情绪,发出火焰到来之前的青烟,在火焰产生的那一瞬间,或者火焰自己腾空而起,或者借助一只水竹制成的吹火筒,嘴唇中吹出的温热的空气穿过火筒,带着人的心思,与火种接触,火焰产生。
这个过程从不间断,在乡下庸常的日子里重复。重复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不须化太多的心思思考怎样让火焰复原,变得浓郁或更加美丽。因为寻常,成为经验,在双手和大脑同时做着其它的物事的时候,甚至唠叨着日子的不常时,下意识中让火焰腾起,热烈地燃烧。
会过日子的人家,火焰都是自燃的,主人只需给灶堂里加一把柴草,让它们自己伸出有形无形的触须,眼睛或手,头发或呼吸,寻找灰烬下面的火种,相互勾起手指,定好暗语;似乎在刚刚需要火焰的时候,青烟就腾起明焰了,然后涮洗干净的铸铁锅发热,红灼,准备接受一瓢清水、一把米面,或一勺菜籽油的到访。
在四季轮回的乡下的岁月中,火焰从未离开过故土一天。它们不走亲戚,不向往更远的天空,驻守在炉塘里,灶堂里,最远蜇伏在地头的荒草间,石头缝里;如果高兴,最多只是努力地探起身子,高过主人的头顶,看一看那称做人的主人的表情。火焰也是察言观色的,它们会看清楚主人的脸堂发出红润,变得油光水华,那么它们会更加明艳地把主人的脸堂勾勒成丰富的沟壑、庄稼的土垄、林木的葱茏、河溪中摇曳的水影,使之富有内涵。如果人的脸色阴郁呢?火焰变幻频道,甚至频率,它们压低身姿,像倾听,或推心置腹的勾通,回应人的叹息或沉默,火焰会用自己的明暗表达美好或者落寞。乡下人总结,人显俏,火也笑;人耸柴火湿,没得早饭吃。
在乡下耕种得熟稔的土地上,火焰从春天就开始劳作,扯起四个季节的旗帜,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号召乡下的植物回到地头。春天烧地荒,初夏烧火粪,秋天烧秸秆,冬天烧暖和。乡下把冬天的火焰,称做烤火斑:在冬翻的地头,火焰给翻地的农人做伴,让土地翻出水汽结出火斑;在农家的屋顶下,火焰是冬天的靠山,烤出农人脚杆上的火斑,让冷清的日子保持饭菜那样的温度。这样的意念久了,我常常感到与其说乡下粮食的清香是来自阳光与水土,还不如直接说是来自乡下那古老的火焰。一把简单的火,在春天烧去轮歇地里的荒草,荒草化成草木灰,等待一个冬天的种子,落进草木灰中,然后雨水接踵而至,种子发芽,抽条,长成高大的庄稼。好粮食都是火焰种出来的,有火焰的热烈的香。
知晓乡村生活的人,可能都明白,正经的庄稼人,为什么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不颐指气使,他们一定是按照种子的暗示,安排土地的翻耕,谋算雨水的降临--再好的一块地,他们都会安排土地的轮歇,即便是肥沃的水田,在四个季节里,他们叫水田在冬天里歇一个长假,让泥巴与冬水融合,像一家人一样整日低低私语,构思明年的水稻怎么生长、无病无灾、取得丰收。在轮歇地里,无论是包谷,还是小麦,也或平凡无丁点名气的小杂粮,如红小豆、豌胡豆、荞麦、燕麦,它们常常长得油气十足,这样的粮食叫人心高气傲。
再比如洋芋,作为乡下的大料作物,可以当得农家半个家当。上品的洋芋必须生长于高地,与林木接壤,伸手可以触得云朵。我所结识的最丰硕不已的洋芋都生长于轮歇地,那样的地由火焰翻耕,草木灰深厚,高地上的阳光、空气、水是那么稠密地眷顾着这些铺地而生的绿色植物,火焰消失后将澎湃的力量转存于地下,赋予给土地那些细小的颗粒,托着种子的梦想向上腾越,阳光的力量从高空向下倾泻,怂恿洋芋的块茎在绿叶之下,汹涌地膨胀,不歇地扩大自己的疆土,长成了高山洋芋古往今来的好名声。
再比如,即便是种过冬油菜、冬小麦的起旱的水田,当油菜和小麦收过之后,农人一定要固执地把油菜、小麦的秸秆当田焚烧,让它们以灰烬的形式重回土地。在认真经营的水田里,那些老得模糊了时间来路的深水田,或者新开出的旱梆田,驻水之后,你都能看到勤快的农人背来青肥,沤在田里,那样的青肥,是初夏刚刚长成的青枝嫩叶,农人似乎是把整个春夏的绿色都挪到田里了,水与青草精巧谋划,蓄积骚动的力量和场景,等待着谷种君临。那时,正是一年中最光荣的季节,雨水丰沛,太阳的角度正好经历早晨与傍晚的全过程,它们以火焰般明丽的自由身姿涌入田里,让水燃烧,让青肥燃烧,这样的故土,还有什么庄稼不能功成名就呢!
我曾经非常感动乡村的婚礼。新媳妇的陪嫁里,最着名的不是金银财富,不是漆光闪闪的八抬家具,不是新衣铺盖,是所有带箱斗的家具中一律填满的各色庄稼的种子。凡是乡下生长的,叫得上名子的,正经能上桌面的、能添进饭碗的,都要从娘家带入婆家。看一队送嫁人行走在乡间的大路上,八抬也好,十二抬也好,二十四抬也好,都不能说明问题,窍门在已然刷过新的红漆的喜杠在行进中上下忽闪的程度,嫁妆的重量是无言的骄傲。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壮硕的抬喜妆的汉子一定满头大汗,敞开胸怀大口喘气,一边高兴地责骂送嫁的上亲心太狠,恨不得把一座粮仓都抬过去。这个向晚的婚宴热烈非凡,出力的汉子们会以酒遮脸,装疯卖傻,一定会有一个两个嘴巴不饶人的上亲大醉于他们亲家公的大堂。
可能现在很多人会不解,除了粮食的种子随嫁,另有一样东西:火,火的种子,也是随嫁的重要成员。可以没有太多的家具、铺陈、银钱、里外三新的新衣随嫁,除了粮食的种子,火随人走--最小门小户的人家嫁女,也不敢忘了火种。再早,讲究的人家专一新打制了铜火盆,盛装了娘家人的灰烬,灰烬下埋着娘家人的火种;再后是新制的火镰,随带一团精心刮制的竹茸、娘家的火纸捻。最后是火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最流行的是“宁强火柴”,有两种版本,素装无图案,是为百姓家常用,有漂亮图案的是干部或讲究的人家用,专一用来点灯、点火抽烟,出没于重要场面。随嫁无论如何都是有漂亮图案的那种,精心择选了,确保根根能划燃。
很多年里,乡下新人进门,还兴在大门口摆一个大火盆,火炭明白地烧着,指示着家道兴旺的众多寄托。新嫁娘需要从火盆上跨过,夸张而认真,赢得围观者的赞叹。也有要跨一副马鞍的,寓意平安,很多传闻中有,我从未见过。关键是跨火盆,寓言着从此男家香火鼎盛,子孙万代,六畜兴旺。
我有时傻想,那从娘家带去的火种最后怎样派上用场呢?是要点燃到婆家后新嫁娘第一回独自操作的第一顿饭的灶火吗?第一个重要的新婚之夜新人睡房里的那盏见证一个乡下女子人生转折的灯,是随嫁的火种点燃的吗?自此两家的火种融合为一,再不熄灭,在每一个日子被保留,在需要的时候燃起火焰?
假如你在荒僻之地走长途,看到了烟雾从半天里升起,或一道山梁后露出头,那就是说你快到一个村庄了。那烟雾多半是早晨、正午或晚间的炊烟,准时升起。炊烟是乡村的品牌。浪漫而真实。一个行走的人,到了脚杆发软的时候,希望看到那亲切的炊烟。一个坚强的行人,看到诱惑的炊烟,脚杆怎么能不发软!我在乡下小住时,最喜欢看一天中的三次炊烟,它们款然上升,然后停在半空,聚积成阴影,当阴影越聚越多的时候,说明所有劳作的人已然回到了家中,当阴影渐渐飘散之后,说明汤汤饭饭已然滋润了劳动者的肠胃,他们在饭后会放下身子,眯瞪一会子,享受片刻的清闲--而狗子还在叫吠,猪还在声唤,鸡群还在竹林下集体午休,发出小雨一般的鼾声,女人尖厉的嗓门还在响起,小娃的声音也如翻花的泉水,在村巷和人家的墙头下水淋淋四溅。
这样的时候,我常常陷入痴迷:比如想到庄稼从第一粒种子开始,疯狂地在田园上漫延,它们像风一般刮过乡村,一次次形成风暴。比如一把米面,怎样与清水一道,在锅底的火焰创作下,变得甜软香糯,它们怎么走进我们的肠胃,化作我们身体里的火焰,然后演绎成我们表情里的风景。我常常有如此的感受:在乡下正经的吃饭,比如把脸埋进碗里,精力集中,牙齿有力地切咬,舌头有板有眼地拌和,听到每一口饭菜明明白白地落进肚腔,重重地砸到胃的地面上,空谷回音,叫人生疼,然后汗腺大开,头上蒸起云雾,满脸淌汗,汗流浃背,当恋恋不舍地放下碗筷,要做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望空长啸一声,然后归于踏实。在乡下吃一顿饭,就进入一个境界,感激粮食与火焰,感激依然生气勃勃的肠胃。
我走在很多的乡村安居点,也深深油然想起乡下的炊烟。由炊烟而火焰。我想起那些在乡下被珍藏的火种,它们睁着红亮的眸子,放着蓝汪汪的如水色般的光芒,并分明感受到了那些火焰的热度与灼人。很多已然搬离老屋的从前活跃于丰饶的故土的老人们,离得再远,每年都会找些借口,回到几十里、上百里的老屋去看一看:这样的情景我亲身经见,老屋人走村空,土地重新为树木与荒草占住,大片的轮歇地,如今早已飞籽成林。不再有人耕种的老田,水柳与蓼草并生,成为麻雀、点水雀、豌豆雀的天堂;随迁不走的斑鸠,在水竹林里高一声低一声歌唱着岁月的永恒,进而像一片乌云刮起,席卷过空廓的乡村的上空。一只老鹰孤傲地在高空盘旋,长长的影子在山林间移动、扫射,久久徘徊不落。那些离开熟悉的土地的老人们,他们回到从前生活的故土,该有那一只鹰一样的心境吗?他们不再能像保留火种那样,保留土地上四季轮回的依恋,以及土地上留下的往事,他们的表情也像长空那般空廓、宁静吗?
在灶塘里,在堂屋的火炉坑里,埋下火种,时间变成灰烬,灰烬下面是火的种子。每顿乡下的汤汤饭饭完毕,灶膛里最后不用退出的火炭,留成了火种。堂屋火炉坑里的火种亦然,在乡下的夜色深静,狗声停吠,最耐守夜的老人都打起接二连三的呵欠之后,没烧尽的劈柴退出,红火灰里的火种留下。火种被燃烧过的炭灰掩埋,进入时间的深处,缓慢地燃烧或发酵。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乡村?他们习惯留火种,习惯再次需要火焰的时候,用干燥的柴草引火。刨开灰烬,让火种与柴草接触,用昨天的火种引燃今天的火焰。然后火焰穿过劈柴,与劈柴一起酝酿情绪,发出火焰到来之前的青烟,在火焰产生的那一瞬间,或者火焰自己腾空而起,或者借助一只水竹制成的吹火筒,嘴唇中吹出的温热的空气穿过火筒,带着人的心思,与火种接触,火焰产生。
这个过程从不间断,在乡下庸常的日子里重复。重复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不须化太多的心思思考怎样让火焰复原,变得浓郁或更加美丽。因为寻常,成为经验,在双手和大脑同时做着其它的物事的时候,甚至唠叨着日子的不常时,下意识中让火焰腾起,热烈地燃烧。
会过日子的人家,火焰都是自燃的,主人只需给灶堂里加一把柴草,让它们自己伸出有形无形的触须,眼睛或手,头发或呼吸,寻找灰烬下面的火种,相互勾起手指,定好暗语;似乎在刚刚需要火焰的时候,青烟就腾起明焰了,然后涮洗干净的铸铁锅发热,红灼,准备接受一瓢清水、一把米面,或一勺菜籽油的到访。
在四季轮回的乡下的岁月中,火焰从未离开过故土一天。它们不走亲戚,不向往更远的天空,驻守在炉塘里,灶堂里,最远蜇伏在地头的荒草间,石头缝里;如果高兴,最多只是努力地探起身子,高过主人的头顶,看一看那称做人的主人的表情。火焰也是察言观色的,它们会看清楚主人的脸堂发出红润,变得油光水华,那么它们会更加明艳地把主人的脸堂勾勒成丰富的沟壑、庄稼的土垄、林木的葱茏、河溪中摇曳的水影,使之富有内涵。如果人的脸色阴郁呢?火焰变幻频道,甚至频率,它们压低身姿,像倾听,或推心置腹的勾通,回应人的叹息或沉默,火焰会用自己的明暗表达美好或者落寞。乡下人总结,人显俏,火也笑;人耸柴火湿,没得早饭吃。
在乡下耕种得熟稔的土地上,火焰从春天就开始劳作,扯起四个季节的旗帜,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号召乡下的植物回到地头。春天烧地荒,初夏烧火粪,秋天烧秸秆,冬天烧暖和。乡下把冬天的火焰,称做烤火斑:在冬翻的地头,火焰给翻地的农人做伴,让土地翻出水汽结出火斑;在农家的屋顶下,火焰是冬天的靠山,烤出农人脚杆上的火斑,让冷清的日子保持饭菜那样的温度。这样的意念久了,我常常感到与其说乡下粮食的清香是来自阳光与水土,还不如直接说是来自乡下那古老的火焰。一把简单的火,在春天烧去轮歇地里的荒草,荒草化成草木灰,等待一个冬天的种子,落进草木灰中,然后雨水接踵而至,种子发芽,抽条,长成高大的庄稼。好粮食都是火焰种出来的,有火焰的热烈的香。
知晓乡村生活的人,可能都明白,正经的庄稼人,为什么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不颐指气使,他们一定是按照种子的暗示,安排土地的翻耕,谋算雨水的降临--再好的一块地,他们都会安排土地的轮歇,即便是肥沃的水田,在四个季节里,他们叫水田在冬天里歇一个长假,让泥巴与冬水融合,像一家人一样整日低低私语,构思明年的水稻怎么生长、无病无灾、取得丰收。在轮歇地里,无论是包谷,还是小麦,也或平凡无丁点名气的小杂粮,如红小豆、豌胡豆、荞麦、燕麦,它们常常长得油气十足,这样的粮食叫人心高气傲。
再比如洋芋,作为乡下的大料作物,可以当得农家半个家当。上品的洋芋必须生长于高地,与林木接壤,伸手可以触得云朵。我所结识的最丰硕不已的洋芋都生长于轮歇地,那样的地由火焰翻耕,草木灰深厚,高地上的阳光、空气、水是那么稠密地眷顾着这些铺地而生的绿色植物,火焰消失后将澎湃的力量转存于地下,赋予给土地那些细小的颗粒,托着种子的梦想向上腾越,阳光的力量从高空向下倾泻,怂恿洋芋的块茎在绿叶之下,汹涌地膨胀,不歇地扩大自己的疆土,长成了高山洋芋古往今来的好名声。
再比如,即便是种过冬油菜、冬小麦的起旱的水田,当油菜和小麦收过之后,农人一定要固执地把油菜、小麦的秸秆当田焚烧,让它们以灰烬的形式重回土地。在认真经营的水田里,那些老得模糊了时间来路的深水田,或者新开出的旱梆田,驻水之后,你都能看到勤快的农人背来青肥,沤在田里,那样的青肥,是初夏刚刚长成的青枝嫩叶,农人似乎是把整个春夏的绿色都挪到田里了,水与青草精巧谋划,蓄积骚动的力量和场景,等待着谷种君临。那时,正是一年中最光荣的季节,雨水丰沛,太阳的角度正好经历早晨与傍晚的全过程,它们以火焰般明丽的自由身姿涌入田里,让水燃烧,让青肥燃烧,这样的故土,还有什么庄稼不能功成名就呢!
我曾经非常感动乡村的婚礼。新媳妇的陪嫁里,最着名的不是金银财富,不是漆光闪闪的八抬家具,不是新衣铺盖,是所有带箱斗的家具中一律填满的各色庄稼的种子。凡是乡下生长的,叫得上名子的,正经能上桌面的、能添进饭碗的,都要从娘家带入婆家。看一队送嫁人行走在乡间的大路上,八抬也好,十二抬也好,二十四抬也好,都不能说明问题,窍门在已然刷过新的红漆的喜杠在行进中上下忽闪的程度,嫁妆的重量是无言的骄傲。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壮硕的抬喜妆的汉子一定满头大汗,敞开胸怀大口喘气,一边高兴地责骂送嫁的上亲心太狠,恨不得把一座粮仓都抬过去。这个向晚的婚宴热烈非凡,出力的汉子们会以酒遮脸,装疯卖傻,一定会有一个两个嘴巴不饶人的上亲大醉于他们亲家公的大堂。
可能现在很多人会不解,除了粮食的种子随嫁,另有一样东西:火,火的种子,也是随嫁的重要成员。可以没有太多的家具、铺陈、银钱、里外三新的新衣随嫁,除了粮食的种子,火随人走--最小门小户的人家嫁女,也不敢忘了火种。再早,讲究的人家专一新打制了铜火盆,盛装了娘家人的灰烬,灰烬下埋着娘家人的火种;再后是新制的火镰,随带一团精心刮制的竹茸、娘家的火纸捻。最后是火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最流行的是“宁强火柴”,有两种版本,素装无图案,是为百姓家常用,有漂亮图案的是干部或讲究的人家用,专一用来点灯、点火抽烟,出没于重要场面。随嫁无论如何都是有漂亮图案的那种,精心择选了,确保根根能划燃。
很多年里,乡下新人进门,还兴在大门口摆一个大火盆,火炭明白地烧着,指示着家道兴旺的众多寄托。新嫁娘需要从火盆上跨过,夸张而认真,赢得围观者的赞叹。也有要跨一副马鞍的,寓意平安,很多传闻中有,我从未见过。关键是跨火盆,寓言着从此男家香火鼎盛,子孙万代,六畜兴旺。
我有时傻想,那从娘家带去的火种最后怎样派上用场呢?是要点燃到婆家后新嫁娘第一回独自操作的第一顿饭的灶火吗?第一个重要的新婚之夜新人睡房里的那盏见证一个乡下女子人生转折的灯,是随嫁的火种点燃的吗?自此两家的火种融合为一,再不熄灭,在每一个日子被保留,在需要的时候燃起火焰?
假如你在荒僻之地走长途,看到了烟雾从半天里升起,或一道山梁后露出头,那就是说你快到一个村庄了。那烟雾多半是早晨、正午或晚间的炊烟,准时升起。炊烟是乡村的品牌。浪漫而真实。一个行走的人,到了脚杆发软的时候,希望看到那亲切的炊烟。一个坚强的行人,看到诱惑的炊烟,脚杆怎么能不发软!我在乡下小住时,最喜欢看一天中的三次炊烟,它们款然上升,然后停在半空,聚积成阴影,当阴影越聚越多的时候,说明所有劳作的人已然回到了家中,当阴影渐渐飘散之后,说明汤汤饭饭已然滋润了劳动者的肠胃,他们在饭后会放下身子,眯瞪一会子,享受片刻的清闲--而狗子还在叫吠,猪还在声唤,鸡群还在竹林下集体午休,发出小雨一般的鼾声,女人尖厉的嗓门还在响起,小娃的声音也如翻花的泉水,在村巷和人家的墙头下水淋淋四溅。
这样的时候,我常常陷入痴迷:比如想到庄稼从第一粒种子开始,疯狂地在田园上漫延,它们像风一般刮过乡村,一次次形成风暴。比如一把米面,怎样与清水一道,在锅底的火焰创作下,变得甜软香糯,它们怎么走进我们的肠胃,化作我们身体里的火焰,然后演绎成我们表情里的风景。我常常有如此的感受:在乡下正经的吃饭,比如把脸埋进碗里,精力集中,牙齿有力地切咬,舌头有板有眼地拌和,听到每一口饭菜明明白白地落进肚腔,重重地砸到胃的地面上,空谷回音,叫人生疼,然后汗腺大开,头上蒸起云雾,满脸淌汗,汗流浃背,当恋恋不舍地放下碗筷,要做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望空长啸一声,然后归于踏实。在乡下吃一顿饭,就进入一个境界,感激粮食与火焰,感激依然生气勃勃的肠胃。
我走在很多的乡村安居点,也深深油然想起乡下的炊烟。由炊烟而火焰。我想起那些在乡下被珍藏的火种,它们睁着红亮的眸子,放着蓝汪汪的如水色般的光芒,并分明感受到了那些火焰的热度与灼人。很多已然搬离老屋的从前活跃于丰饶的故土的老人们,离得再远,每年都会找些借口,回到几十里、上百里的老屋去看一看:这样的情景我亲身经见,老屋人走村空,土地重新为树木与荒草占住,大片的轮歇地,如今早已飞籽成林。不再有人耕种的老田,水柳与蓼草并生,成为麻雀、点水雀、豌豆雀的天堂;随迁不走的斑鸠,在水竹林里高一声低一声歌唱着岁月的永恒,进而像一片乌云刮起,席卷过空廓的乡村的上空。一只老鹰孤傲地在高空盘旋,长长的影子在山林间移动、扫射,久久徘徊不落。那些离开熟悉的土地的老人们,他们回到从前生活的故土,该有那一只鹰一样的心境吗?他们不再能像保留火种那样,保留土地上四季轮回的依恋,以及土地上留下的往事,他们的表情也像长空那般空廓、宁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