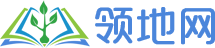灵魂的彼岸
发布者:杪夏十久
时间:2022-11-15 22:35
沉浸在浩瀚的夜里,失眠的神经在寂静的黑暗中享受着孤独。渐渐的,熬过了零点的灵魂在过去与黎明的临界中,挣扎过了当天的门槛。当灵魂痛快的褪去了面具,无拘无束的坦露出本真,与深夜拥抱并水乳交融的时候,思维俨然成了八面玲珑的鼓乐,在灵魂的摩擦、敲打、穿越下,形成一环环性灵、理智和梦幻纠结成多维立体的波纹,弥漫流散,畅游、飞翔在无穷的天际。
在这样后凌晨的夜里,夜是魔方,孤独者的舞台,性灵的花园,梦幻的方舟。夜幕已经把物质世界的一切,钢筋水泥、玻璃幕墙、车辆、街道,等白天你要躲避的,钝迟的、尖锐的,包括声音、影像所卵生出的恐怖、狰狞、虚伪、漠然、痛苦都挡在都挡在了意识之外。此刻,我的思维或者是性灵不再是白天的孤独了,即使孤独也是一种迷幻的享受。我似乎清晰的听到了灵魂在蠢动的萌芽,生长、低吟和歌唱。
这黑黑的夜里,睁开双眼和闭着双眼都是一样的黑。可我,还是习惯的让双眼微闭。记得一首歌词里说过“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可见,沉浸在黑夜是一种享受。睁开眼睛看世界,感官的世界和虚拟的意识,无疑也会错生出几许的烦恼、不安,痛苦甚至苦难。
我的灵魂在散步,灵魂的触角感受到夜的轻盈、悠远。轻轻转身的刹那,听到了一个天真的声音,一个男孩的声音,“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声音来自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和城市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破天惊的声音。此刻,皇帝、大臣、围观的百姓都是惊诧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皇帝的新装》故事里男孩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着。我一直觉得,这个声音不是1837年从安徒生的笔下发出的,在童真的世界本来就一直有这个声音。只不过安徒生把这个声音描述的更具体,更真切,更加让皇帝、大臣、围观的百姓听得清楚并承认这个声音。
童话的世界是美妙的,可童年的故事又是懵懵懂懂的,回忆容易使人错乱和混淆。我想起我也和《皇帝的新装》里的男孩一样喊出过类似的声音。
童年的眼睛总是看的很清,很亮。我在麦收的夏夜,看到一个影子把生产队打麦场上装满小麦的麻袋偷偷的扛回家,那个影子是村里的王贵时。有一个声音就像胀满小肚子里的尿一样,总要尿出来才痛快。王贵,和中学课本《王贵与李香香》里闹革命报杀父深仇的主人公王贵重名的庄稼汉子。一年到头整天的拿着一把镰刀,在庄稼地来回晃悠“看青人”。第二天的晌午,我听到队里做事认真的会计说昨晚打麦场上丢了一麻袋麦子,大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我似乎憋了一晚上的尿终于射出来 “我看见王贵把一个麻袋扛回自己家了”。我的话说出来后,人群中死一般的寂静。大人们看我的眼光是我从没有过的异样,诧异、猜测、愤怒、责问、无奈,只是没有鼓励。柳树上的知了一直喊着“知了、知了”。
富贵的宫殿,神奇的新装,乡村的麦场,大臣,百姓,童言无忌的男孩,所有的镜像在灵魂的夜空幻灯一般演绎着。安徒生没有交代穿了新装的皇帝,经男孩石破天惊的真话之后的结局。但我可以想象,皇帝所统治的国家,或者是渐渐地变成无声的世界,或者是勇敢地处置了故事中那两个天才的裁缝,但是或者似乎是不可能的结局。童话里男孩的声音终究传播了千年、百年,稚嫩的童声,在吵杂喧嚣的世界中湮没着,就像我当年的声音一样是微不足道,很多人听见了也是没有结果的。抑或,在这样的深邃的夜空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匿着这种声音,不知是呐喊还是低吟或者永远的沉默。我推测着我内向沉默性格的一面,是不是因为那个夏天人群中死一般沉静之后的影响有关。
想到这些,我的灵魂不禁有些懊悔和沮丧。夜愈发的茂盛,茁壮。我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呼吸渐渐地由平缓到铿锵和有力,灵魂在这样的夜里挥舞着有力的翅膀,穿越起来。夜幕似乎被灵魂撕开了一隙裂痕。所以,我还是不可避免的看到了白天压抑的让人视觉错乱的高楼大厦,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阳光照射衍生的龃龉错杂中拥挤的车辆,喧嚣的人群。甚至还看到了现代城市生活光鲜背后隐匿的灰暗的一面。我的灵魂不敢在这样的氛围久留,我的呼吸愈发的加快,甚至有些心悸了。我还是回到了夜幕里,奔跑的灵魂看到夜空下的山峰原野,是错落突兀的深浅的墨黑。原来,在夜里山峰毕竟是山峰,有突兀于原野的深刻夜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千年前的苏轼在丘壑纵横、峰峦起伏的庐山胜地,就发出这样哲理性的感叹。我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眼中的景物和感悟就可以大相径庭。在千年的感叹声中,我试图寻求一种镶嵌在白天与黑夜之中的神奇力量,作为灵魂永久的理想花园,让灵魂不再孤独和压抑,并且能让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沿着夜幕到天地之间共鸣。
我承认,这是我浪漫主义甚至是轻狂的天真。因为千年前吟啸官场和江湖一生的苏轼,挂冠于哲学、佛学、文学的殿堂寻觅和辗转一生,最终也只能浪漫的把灵魂归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对灵魂彼岸的渴望,抑或无奈。
当浪漫成为一种最终的归隐,理想的桃园就是看得见的彼岸。我的性灵在黎明前的夜幕不再压抑,变得饱满和丰盈,有节律的飞翔起来。
正是天高气爽,云淡日丽的秋天。我在万里霜天香飘四野的菊园行走,心灵的天空,没有一点儿阴霾和浮云。心旷神怡的性灵不经意间舒展开翅膀,到达理想的彼岸。我和近两千年前的陶渊明在开满菊花的田园饮酒放歌。陶公告诉我,他的世外桃园,是他营造的人间生活的理想境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顺着陶公的手势,我真切的看到了陶公指向的南山有着陶公祖先的墓碑,也似乎看到了他的桃花源。陶公的南山可能是陶公灵魂的最终归宿,他的桃园也许只能在灵魂的天国实现。
我耳闻目睹了陶公的桃园世界,灵魂的翅膀从容闲适。思维也敏捷开阔。陶公的桃园世界,是西方的极乐世界吗?可能是。但是,现在看来是过于理想的世界,脱离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我又展开灵魂的翅膀,飞翔到了两千多年前的雅典。金碧辉煌的雅典果然是典雅与华贵,哥特式的建筑线条优美。中年的哲学家柏拉图,沉稳成熟,举手投足间透着睿智和激情。
我在他的精神世界的宫殿聆听着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国的道德公正,是超越于体制和物质之上的真理和美丽的境界。我对他诗意般的理想唯美,不甚了解。经历了两千多年还没有让人类判断正确与否的理论,我穷其一生也是迷惘的。他纯粹的精神恋爱法,成为超越肉体,没有性爱婚姻的代名词,我却不敢苟同。作为一个正常的饮食男女,一个正常的男人,没有正常性欲的婚姻,在自己意淫的精神世界里高歌,也是和人性相悖的。
我不想让灵魂飞翔了,我的肉体我的心脏已经适应不了在时光的隧道中驰骋。灵魂理智平稳的降落在现实世界。我的脚下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铁路。这是一条横亘东西的动脉,向东经山海之关延伸到遥远的东方,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向西,遥远的雪域高原,那里有喜马拉雅和布达拉宫,世界的第三极,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就在那里起航,有我心中最圣洁的雪莲花,有流传了三百年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和情人仓央嘉措。我站在铁轨上,铁轨横卧在大地,犹如大地之上的坚挺有力的脉搏。我听到远处的火车在大地上铿锵疾驰的声音,车轮挤压铁轨的长鸣,在夜空中犹如通向天堂的号角。
遥远的两千多年前,统一了整个中国的神一般的秦始皇,也在这里挥鞭赶山怒填仓海,高呼着“大地在我脚下”。他可以创建千秋伟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他源于对生命更有理想的追求和渴望。面对着遥遥的渤海,企图寻求长生不老的良方,做一个永远的人间神仙。可如今,斯人已逝,只有长城,在山海之巅矗立延伸。
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忧郁的沉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有些唏嘘,诗人海子,当火车从他身上轰鸣碾压过去的刹那,他的灵魂沿着黑夜中铁轨的阶梯,升入天堂的刹那,是不是看到了大海的彼岸,桃源般的花开似锦。
这一切的一切。看见与否,终究都是彼岸。
在这样后凌晨的夜里,夜是魔方,孤独者的舞台,性灵的花园,梦幻的方舟。夜幕已经把物质世界的一切,钢筋水泥、玻璃幕墙、车辆、街道,等白天你要躲避的,钝迟的、尖锐的,包括声音、影像所卵生出的恐怖、狰狞、虚伪、漠然、痛苦都挡在都挡在了意识之外。此刻,我的思维或者是性灵不再是白天的孤独了,即使孤独也是一种迷幻的享受。我似乎清晰的听到了灵魂在蠢动的萌芽,生长、低吟和歌唱。
这黑黑的夜里,睁开双眼和闭着双眼都是一样的黑。可我,还是习惯的让双眼微闭。记得一首歌词里说过“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可见,沉浸在黑夜是一种享受。睁开眼睛看世界,感官的世界和虚拟的意识,无疑也会错生出几许的烦恼、不安,痛苦甚至苦难。
我的灵魂在散步,灵魂的触角感受到夜的轻盈、悠远。轻轻转身的刹那,听到了一个天真的声音,一个男孩的声音,“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声音来自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和城市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破天惊的声音。此刻,皇帝、大臣、围观的百姓都是惊诧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皇帝的新装》故事里男孩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着。我一直觉得,这个声音不是1837年从安徒生的笔下发出的,在童真的世界本来就一直有这个声音。只不过安徒生把这个声音描述的更具体,更真切,更加让皇帝、大臣、围观的百姓听得清楚并承认这个声音。
童话的世界是美妙的,可童年的故事又是懵懵懂懂的,回忆容易使人错乱和混淆。我想起我也和《皇帝的新装》里的男孩一样喊出过类似的声音。
童年的眼睛总是看的很清,很亮。我在麦收的夏夜,看到一个影子把生产队打麦场上装满小麦的麻袋偷偷的扛回家,那个影子是村里的王贵时。有一个声音就像胀满小肚子里的尿一样,总要尿出来才痛快。王贵,和中学课本《王贵与李香香》里闹革命报杀父深仇的主人公王贵重名的庄稼汉子。一年到头整天的拿着一把镰刀,在庄稼地来回晃悠“看青人”。第二天的晌午,我听到队里做事认真的会计说昨晚打麦场上丢了一麻袋麦子,大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我似乎憋了一晚上的尿终于射出来 “我看见王贵把一个麻袋扛回自己家了”。我的话说出来后,人群中死一般的寂静。大人们看我的眼光是我从没有过的异样,诧异、猜测、愤怒、责问、无奈,只是没有鼓励。柳树上的知了一直喊着“知了、知了”。
富贵的宫殿,神奇的新装,乡村的麦场,大臣,百姓,童言无忌的男孩,所有的镜像在灵魂的夜空幻灯一般演绎着。安徒生没有交代穿了新装的皇帝,经男孩石破天惊的真话之后的结局。但我可以想象,皇帝所统治的国家,或者是渐渐地变成无声的世界,或者是勇敢地处置了故事中那两个天才的裁缝,但是或者似乎是不可能的结局。童话里男孩的声音终究传播了千年、百年,稚嫩的童声,在吵杂喧嚣的世界中湮没着,就像我当年的声音一样是微不足道,很多人听见了也是没有结果的。抑或,在这样的深邃的夜空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匿着这种声音,不知是呐喊还是低吟或者永远的沉默。我推测着我内向沉默性格的一面,是不是因为那个夏天人群中死一般沉静之后的影响有关。
想到这些,我的灵魂不禁有些懊悔和沮丧。夜愈发的茂盛,茁壮。我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呼吸渐渐地由平缓到铿锵和有力,灵魂在这样的夜里挥舞着有力的翅膀,穿越起来。夜幕似乎被灵魂撕开了一隙裂痕。所以,我还是不可避免的看到了白天压抑的让人视觉错乱的高楼大厦,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阳光照射衍生的龃龉错杂中拥挤的车辆,喧嚣的人群。甚至还看到了现代城市生活光鲜背后隐匿的灰暗的一面。我的灵魂不敢在这样的氛围久留,我的呼吸愈发的加快,甚至有些心悸了。我还是回到了夜幕里,奔跑的灵魂看到夜空下的山峰原野,是错落突兀的深浅的墨黑。原来,在夜里山峰毕竟是山峰,有突兀于原野的深刻夜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千年前的苏轼在丘壑纵横、峰峦起伏的庐山胜地,就发出这样哲理性的感叹。我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眼中的景物和感悟就可以大相径庭。在千年的感叹声中,我试图寻求一种镶嵌在白天与黑夜之中的神奇力量,作为灵魂永久的理想花园,让灵魂不再孤独和压抑,并且能让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沿着夜幕到天地之间共鸣。
我承认,这是我浪漫主义甚至是轻狂的天真。因为千年前吟啸官场和江湖一生的苏轼,挂冠于哲学、佛学、文学的殿堂寻觅和辗转一生,最终也只能浪漫的把灵魂归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对灵魂彼岸的渴望,抑或无奈。
当浪漫成为一种最终的归隐,理想的桃园就是看得见的彼岸。我的性灵在黎明前的夜幕不再压抑,变得饱满和丰盈,有节律的飞翔起来。
正是天高气爽,云淡日丽的秋天。我在万里霜天香飘四野的菊园行走,心灵的天空,没有一点儿阴霾和浮云。心旷神怡的性灵不经意间舒展开翅膀,到达理想的彼岸。我和近两千年前的陶渊明在开满菊花的田园饮酒放歌。陶公告诉我,他的世外桃园,是他营造的人间生活的理想境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顺着陶公的手势,我真切的看到了陶公指向的南山有着陶公祖先的墓碑,也似乎看到了他的桃花源。陶公的南山可能是陶公灵魂的最终归宿,他的桃园也许只能在灵魂的天国实现。
我耳闻目睹了陶公的桃园世界,灵魂的翅膀从容闲适。思维也敏捷开阔。陶公的桃园世界,是西方的极乐世界吗?可能是。但是,现在看来是过于理想的世界,脱离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我又展开灵魂的翅膀,飞翔到了两千多年前的雅典。金碧辉煌的雅典果然是典雅与华贵,哥特式的建筑线条优美。中年的哲学家柏拉图,沉稳成熟,举手投足间透着睿智和激情。
我在他的精神世界的宫殿聆听着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国的道德公正,是超越于体制和物质之上的真理和美丽的境界。我对他诗意般的理想唯美,不甚了解。经历了两千多年还没有让人类判断正确与否的理论,我穷其一生也是迷惘的。他纯粹的精神恋爱法,成为超越肉体,没有性爱婚姻的代名词,我却不敢苟同。作为一个正常的饮食男女,一个正常的男人,没有正常性欲的婚姻,在自己意淫的精神世界里高歌,也是和人性相悖的。
我不想让灵魂飞翔了,我的肉体我的心脏已经适应不了在时光的隧道中驰骋。灵魂理智平稳的降落在现实世界。我的脚下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铁路。这是一条横亘东西的动脉,向东经山海之关延伸到遥远的东方,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向西,遥远的雪域高原,那里有喜马拉雅和布达拉宫,世界的第三极,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就在那里起航,有我心中最圣洁的雪莲花,有流传了三百年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和情人仓央嘉措。我站在铁轨上,铁轨横卧在大地,犹如大地之上的坚挺有力的脉搏。我听到远处的火车在大地上铿锵疾驰的声音,车轮挤压铁轨的长鸣,在夜空中犹如通向天堂的号角。
遥远的两千多年前,统一了整个中国的神一般的秦始皇,也在这里挥鞭赶山怒填仓海,高呼着“大地在我脚下”。他可以创建千秋伟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他源于对生命更有理想的追求和渴望。面对着遥遥的渤海,企图寻求长生不老的良方,做一个永远的人间神仙。可如今,斯人已逝,只有长城,在山海之巅矗立延伸。
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忧郁的沉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有些唏嘘,诗人海子,当火车从他身上轰鸣碾压过去的刹那,他的灵魂沿着黑夜中铁轨的阶梯,升入天堂的刹那,是不是看到了大海的彼岸,桃源般的花开似锦。
这一切的一切。看见与否,终究都是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