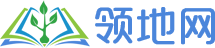人淡如菊,落花无言
发布者:中华七剑
时间:2022-11-15 22:35
小学到初中,父亲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家里常年只剩我与母亲。那时家里有一间比较大的屋子,计划做客厅的,但是一直迟迟没有收拾。因为父母都很忙。父亲开学后在学校工作,放假了还得在省城的美院学习他很热爱的油画。所以那间屋子一直堆放着两个书柜和一张大沙发,还有散落在屋角的几麻袋粮食。平时放学之后若没有其它事,这里便是我的天堂。从书柜里找出小说,然后缩倦在大沙发的角落里,一页一页读,不知屋外时光,眼前是故事里陌生而美好的世界,我追随里面人物的足迹,不知疲倦。只有时时飘绕在鼻翼的粮食清香,提醒我这是在自己家里的某个地方,那粮食,是我母亲春种秋收得来的。
彼时,母亲往往忙于田间或家务,无暇顾及我,只要我按时完成作业、不闹不生病就行。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一段时间,几乎翻遍了自己较感兴趣的书籍,就在那间屋子的大沙发上。父亲喜欢古典的,史实性的小说,《红楼梦》当然是我首先读完了的,接下来是白话的《聊斋》。其实白话并不好看,这是后来朋友送我《聊斋志异》,读后得出的结论。当时也就知道这世界并不只在这间屋子,或者我的家,或者学校,或者远到父亲的工作地。世界是一处美妙的场所,有前有后,前的,叫古代,后的,叫未来,这些都不在我的经验范围;世界非常大,还有许多稀奇美丽的国家,被山,被海,被道路,它们像不规则的格子一样,将人们阻隔,那些国家叫外国,外国人长得不与我们相同,外国人写的书很好看。
记忆中那是一个涂了橘黄油漆的书柜,还是父亲抽空涂上的油漆。它旁边一个是奶油色的,它们造型不一样。橘黄色分上下两部分。上面又分别被分三层,书籍是父亲整理过的次序。最上一层是古典小说,中层是历史小说,下层是外国小说,有《屠格涅夫小说选》、《亚非拉短篇小说选》、《苦难的历程》,《世界通史》,偶尔也有哲学书籍,不多。
橘黄色书柜的下一部分又另看了两扇门,里面分两层,放了一大堆连环画,也有《画报》和油画类刊物,它们在里面整整齐齐的堆放着,但每次都被我翻乱,这是父亲每次整理书柜气恼的原因之一。每次回来,父亲总要整理它,然后修理被我弄坏的书页。沉着脸。那时父亲不赞成我读小说、古典诗词这些,每次听到他要回家的消息,我先藏起手边的书籍,怕他发现,若被他发现我在四册《历代诗歌选》的书页上涂涂写写,非挨一顿打不可。
住在另一个书柜里的,是整部的《二十四史》,我看不懂。除了正史,间或也有一些古人写的野史,偶尔翻开,觉得新鲜有趣,便看几日。尤其里面写一些女子的,或者后宫的,因为插图很好看,可以拿来做有趣的临摹。而且里面女人们的名字一般都婉约精致,住的宫苑名更好听。那时,古典装束的女子一直是我心目中美好女子的样子。
间或碰见父亲封皮柔和的笔记本,也乘他不在悄悄看一下,里面是他写的诗词,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父亲喜用黑色墨水写字,字体端方又不羁,好似水墨画一般,往往在一首诗左下角习惯画一些钢笔画,他的钢笔画真的很好看,往往是一些小动物,或者花卉,父亲最喜欢画的花卉是梅花。黑色钢笔画梅,风骨泠然,却又清丽脱俗。
水墨画一样的字体,当然对当时的我来说很难辨认,所以不知道他写了什么。大致是乡土人情吧。因为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就有他发表在报纸上的诗歌,编辑配以藏族女子或者格桑花……幼时哥哥指给我看这些,看到珍重的铅字排版,虽不懂,却很为父亲骄傲。记得当时那张写字台最下面铺着一整副淡蓝皱纹纸,然后左上角放了父亲发表的部分文字,中间是全家人的照片,也有我们姊妹的。其中一张是哥哥十岁左右和他的伙伴在草原上的照片,穿着温暖的羊皮袄,笑容灿烂极了。哥哥说那是父亲同事的儿子。我的小侄子两岁左右时那照片还在,他指着说那是爸爸(我哥哥)和他(他自己)。当时我们都笑。
老照片,父亲写草原,写蓝天的文字,都在蓝色皱纹纸上,在下午阳光下安静绽放,蓝色逐渐褪色,不会褪色的是宝贵的字迹。蓝色皱纹纸上还有少年时的哥哥写的诗歌。哥哥十二岁时写下:太阳的金箭\射向清晨的草原……发表了,得到稿酬,哥哥决意拿去和他的弟兄们玩儿,而父亲要他收藏它,最后遵循了谁的意思,不得而知。
曾经家里的杂物间是我的最爱(看到《呼兰河传》里萧红也有此嗜好,不禁莞尔),我在那里找到姐姐小时候的读物——《儿童文学》,坐在灰尘扑鼻的书堆上翻看,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从那里读到的。还翻到姐姐初中时填词的本子。一本显然很用心的用白纸订成的大本子,一页一页,是旧词牌下的新诗词。姐姐的钢笔字非常俊秀,简直漂亮,她就这样一页一页写过去,写的多是学习和校园友谊,纯洁清新,写到最后,忽然一句感慨:填词非易事矣……遂搁笔。但是一个本子也就这样写完了。
记忆中那时姐姐非常年轻。鹅蛋脸、杏核眼,乌黑的眼仁,高鼻梁,最美的是那一头乌发,扎两根大辫子,快甩到脚踝了。这样一个会写诗填词又漂亮的女生,不知让多少少年的目光难以拔动呢……后来哥哥爆料说,那时他们老起哄姐姐和一个邻家男孩。我依稀记得那男孩儿,因为他弟弟是我哥哥的同学,叫我小妹妹。弟兄两个都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挺拔。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大家爱拿这件事开姐姐的玩笑,姐姐也不申辩,往往一笑而过。
至今为什么喜欢在夏天喜欢吃玉米,原因是每到暑假兄姊就回家,总带各样精巧的玩物和好吃的给我,教我外面的知识。他们去街上的时候不忘买玉米给我吃,热气腾腾的玉米,来自高原之外的土地,它的味道让我着迷。
每年立秋后兄姊就得回学校。我也该上学了。但是,学校和书籍虽好,终不及他们带给我的外面世界。姐姐教的歌曲,哥哥早雨中喂食鸽子的样子。他们,教我吟诗歌和文字;他们买来玉米给我吃……
所以玉米在记忆中一直是幸福的味道,淡淡的,不可替代。年愈长,味愈浓重。
姐姐曾在合适的年龄和一个男孩相爱。男孩来过我家,喜欢逗我。长得清秀颀长,很温雅。是我母亲心目中女婿的样子。姐姐数学不好,那男孩儿辅导她学数学,她帮人家学语文,便在书桌上相爱了。但当时父母一致说他们家太远,而且那地方太贫穷,怕姐姐受委屈。不赞同。也不知是父亲的意思,还是母亲的想法。不得而知。也不知姐姐是怎么了断了这份感情,亦不得而知。而今她还是那样大说大笑爱热闹的一个人。但是初恋,便也那样断了。
至今姐姐相册里还有那男孩的照片。玉树临风,相片说明的空白处是姐姐秀丽的字迹:C。也不怕姐夫看见、误会。想必姐夫亦是了解的,他们相爱、融洽,对彼此对家人都尊重,体谅,姐夫是一个淳朴而有担当的好男人,姐姐很幸福。
人生漫长,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身边,这种俗世里的幸福,也不亚于那副画吧。但是那副画何其动人。
那副画是这样的。它挂在家里的木头墙壁上。它是父亲的一幅油画,经过精心裱糊的。内容是两个人物在草原上。人物:一男一女,藏族人的装束藏族人的脸,黝黑的脸上有藏族人的快乐,那男子装束简朴、粗犷,悠然坐着,温情地注视爬在他膝前的女孩儿,女孩脸上荡漾着明亮的笑影,衣服褶皱灌满璀璨的阳光。
在她身上,一反那男子的平常,父亲用了最艳丽明亮的色彩,鲜红的珊瑚项链,漆黑发辫上翠绿的头饰,洁白牙齿,宽大袍服里露出葱绿绸衫。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爬在草地上,神情专注地听着左耳畔的录音机……
不知道那里面是何种天籁,如此吸引着她,然后他被她吸引……
父亲一直怀念在草原上做老师的日子,也许,父亲是在怀念青春、怀念岁月、怀念爱情吧。但是父亲告诉我,他中意的女孩其实是汉族,来自北京,他们在读高中时结识。后来呢?我总性急地问后来。后来,她生病,去世了……
淡淡一句,有些黯然。身旁的母亲点点头,神情里有在人世经历风霜后的端肃……原来,母亲早就知道。
一时无语。看父亲。父亲年纪大了,父亲还是最高的个子,温和宽厚的性情,依旧是我心里智慧的,生于1949的父亲。但是在我注视的这一刻,父亲忽然就变成画里的人。聆听天籁,不再看我们。那匣子里的天籁,是什么呢?……
岁月,岁月又是什么呢。
岁月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将从你面前走过,你知道他是唯一与你今生共相伴的,他走过你的账房,牵动你的皮鞭,带走你的歌谣,而你,留不住他。
人生,人生是什么呢,那一对幸福的男女在画中聆听天籁,父亲超逸的精神世界;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父亲踏实的现实世界……人生是什么呢。画中的,超越了现实的琐细停留在纯粹的空间里,却也就流失了现实中的温馨和温暖;现实中的,虽然无法上升至艺术境界的永恒,但是相濡以沫的情感,是由爱情升华的亲情。
亲情,我们此生唯一、贴身的行李。
无论走到哪里,请一定带上它。
彼时,母亲往往忙于田间或家务,无暇顾及我,只要我按时完成作业、不闹不生病就行。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一段时间,几乎翻遍了自己较感兴趣的书籍,就在那间屋子的大沙发上。父亲喜欢古典的,史实性的小说,《红楼梦》当然是我首先读完了的,接下来是白话的《聊斋》。其实白话并不好看,这是后来朋友送我《聊斋志异》,读后得出的结论。当时也就知道这世界并不只在这间屋子,或者我的家,或者学校,或者远到父亲的工作地。世界是一处美妙的场所,有前有后,前的,叫古代,后的,叫未来,这些都不在我的经验范围;世界非常大,还有许多稀奇美丽的国家,被山,被海,被道路,它们像不规则的格子一样,将人们阻隔,那些国家叫外国,外国人长得不与我们相同,外国人写的书很好看。
记忆中那是一个涂了橘黄油漆的书柜,还是父亲抽空涂上的油漆。它旁边一个是奶油色的,它们造型不一样。橘黄色分上下两部分。上面又分别被分三层,书籍是父亲整理过的次序。最上一层是古典小说,中层是历史小说,下层是外国小说,有《屠格涅夫小说选》、《亚非拉短篇小说选》、《苦难的历程》,《世界通史》,偶尔也有哲学书籍,不多。
橘黄色书柜的下一部分又另看了两扇门,里面分两层,放了一大堆连环画,也有《画报》和油画类刊物,它们在里面整整齐齐的堆放着,但每次都被我翻乱,这是父亲每次整理书柜气恼的原因之一。每次回来,父亲总要整理它,然后修理被我弄坏的书页。沉着脸。那时父亲不赞成我读小说、古典诗词这些,每次听到他要回家的消息,我先藏起手边的书籍,怕他发现,若被他发现我在四册《历代诗歌选》的书页上涂涂写写,非挨一顿打不可。
住在另一个书柜里的,是整部的《二十四史》,我看不懂。除了正史,间或也有一些古人写的野史,偶尔翻开,觉得新鲜有趣,便看几日。尤其里面写一些女子的,或者后宫的,因为插图很好看,可以拿来做有趣的临摹。而且里面女人们的名字一般都婉约精致,住的宫苑名更好听。那时,古典装束的女子一直是我心目中美好女子的样子。
间或碰见父亲封皮柔和的笔记本,也乘他不在悄悄看一下,里面是他写的诗词,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父亲喜用黑色墨水写字,字体端方又不羁,好似水墨画一般,往往在一首诗左下角习惯画一些钢笔画,他的钢笔画真的很好看,往往是一些小动物,或者花卉,父亲最喜欢画的花卉是梅花。黑色钢笔画梅,风骨泠然,却又清丽脱俗。
水墨画一样的字体,当然对当时的我来说很难辨认,所以不知道他写了什么。大致是乡土人情吧。因为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就有他发表在报纸上的诗歌,编辑配以藏族女子或者格桑花……幼时哥哥指给我看这些,看到珍重的铅字排版,虽不懂,却很为父亲骄傲。记得当时那张写字台最下面铺着一整副淡蓝皱纹纸,然后左上角放了父亲发表的部分文字,中间是全家人的照片,也有我们姊妹的。其中一张是哥哥十岁左右和他的伙伴在草原上的照片,穿着温暖的羊皮袄,笑容灿烂极了。哥哥说那是父亲同事的儿子。我的小侄子两岁左右时那照片还在,他指着说那是爸爸(我哥哥)和他(他自己)。当时我们都笑。
老照片,父亲写草原,写蓝天的文字,都在蓝色皱纹纸上,在下午阳光下安静绽放,蓝色逐渐褪色,不会褪色的是宝贵的字迹。蓝色皱纹纸上还有少年时的哥哥写的诗歌。哥哥十二岁时写下:太阳的金箭\射向清晨的草原……发表了,得到稿酬,哥哥决意拿去和他的弟兄们玩儿,而父亲要他收藏它,最后遵循了谁的意思,不得而知。
曾经家里的杂物间是我的最爱(看到《呼兰河传》里萧红也有此嗜好,不禁莞尔),我在那里找到姐姐小时候的读物——《儿童文学》,坐在灰尘扑鼻的书堆上翻看,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从那里读到的。还翻到姐姐初中时填词的本子。一本显然很用心的用白纸订成的大本子,一页一页,是旧词牌下的新诗词。姐姐的钢笔字非常俊秀,简直漂亮,她就这样一页一页写过去,写的多是学习和校园友谊,纯洁清新,写到最后,忽然一句感慨:填词非易事矣……遂搁笔。但是一个本子也就这样写完了。
记忆中那时姐姐非常年轻。鹅蛋脸、杏核眼,乌黑的眼仁,高鼻梁,最美的是那一头乌发,扎两根大辫子,快甩到脚踝了。这样一个会写诗填词又漂亮的女生,不知让多少少年的目光难以拔动呢……后来哥哥爆料说,那时他们老起哄姐姐和一个邻家男孩。我依稀记得那男孩儿,因为他弟弟是我哥哥的同学,叫我小妹妹。弟兄两个都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挺拔。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大家爱拿这件事开姐姐的玩笑,姐姐也不申辩,往往一笑而过。
至今为什么喜欢在夏天喜欢吃玉米,原因是每到暑假兄姊就回家,总带各样精巧的玩物和好吃的给我,教我外面的知识。他们去街上的时候不忘买玉米给我吃,热气腾腾的玉米,来自高原之外的土地,它的味道让我着迷。
每年立秋后兄姊就得回学校。我也该上学了。但是,学校和书籍虽好,终不及他们带给我的外面世界。姐姐教的歌曲,哥哥早雨中喂食鸽子的样子。他们,教我吟诗歌和文字;他们买来玉米给我吃……
所以玉米在记忆中一直是幸福的味道,淡淡的,不可替代。年愈长,味愈浓重。
姐姐曾在合适的年龄和一个男孩相爱。男孩来过我家,喜欢逗我。长得清秀颀长,很温雅。是我母亲心目中女婿的样子。姐姐数学不好,那男孩儿辅导她学数学,她帮人家学语文,便在书桌上相爱了。但当时父母一致说他们家太远,而且那地方太贫穷,怕姐姐受委屈。不赞同。也不知是父亲的意思,还是母亲的想法。不得而知。也不知姐姐是怎么了断了这份感情,亦不得而知。而今她还是那样大说大笑爱热闹的一个人。但是初恋,便也那样断了。
至今姐姐相册里还有那男孩的照片。玉树临风,相片说明的空白处是姐姐秀丽的字迹:C。也不怕姐夫看见、误会。想必姐夫亦是了解的,他们相爱、融洽,对彼此对家人都尊重,体谅,姐夫是一个淳朴而有担当的好男人,姐姐很幸福。
人生漫长,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身边,这种俗世里的幸福,也不亚于那副画吧。但是那副画何其动人。
那副画是这样的。它挂在家里的木头墙壁上。它是父亲的一幅油画,经过精心裱糊的。内容是两个人物在草原上。人物:一男一女,藏族人的装束藏族人的脸,黝黑的脸上有藏族人的快乐,那男子装束简朴、粗犷,悠然坐着,温情地注视爬在他膝前的女孩儿,女孩脸上荡漾着明亮的笑影,衣服褶皱灌满璀璨的阳光。
在她身上,一反那男子的平常,父亲用了最艳丽明亮的色彩,鲜红的珊瑚项链,漆黑发辫上翠绿的头饰,洁白牙齿,宽大袍服里露出葱绿绸衫。她像个小女孩一样爬在草地上,神情专注地听着左耳畔的录音机……
不知道那里面是何种天籁,如此吸引着她,然后他被她吸引……
父亲一直怀念在草原上做老师的日子,也许,父亲是在怀念青春、怀念岁月、怀念爱情吧。但是父亲告诉我,他中意的女孩其实是汉族,来自北京,他们在读高中时结识。后来呢?我总性急地问后来。后来,她生病,去世了……
淡淡一句,有些黯然。身旁的母亲点点头,神情里有在人世经历风霜后的端肃……原来,母亲早就知道。
一时无语。看父亲。父亲年纪大了,父亲还是最高的个子,温和宽厚的性情,依旧是我心里智慧的,生于1949的父亲。但是在我注视的这一刻,父亲忽然就变成画里的人。聆听天籁,不再看我们。那匣子里的天籁,是什么呢?……
岁月,岁月又是什么呢。
岁月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将从你面前走过,你知道他是唯一与你今生共相伴的,他走过你的账房,牵动你的皮鞭,带走你的歌谣,而你,留不住他。
人生,人生是什么呢,那一对幸福的男女在画中聆听天籁,父亲超逸的精神世界;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父亲踏实的现实世界……人生是什么呢。画中的,超越了现实的琐细停留在纯粹的空间里,却也就流失了现实中的温馨和温暖;现实中的,虽然无法上升至艺术境界的永恒,但是相濡以沫的情感,是由爱情升华的亲情。
亲情,我们此生唯一、贴身的行李。
无论走到哪里,请一定带上它。